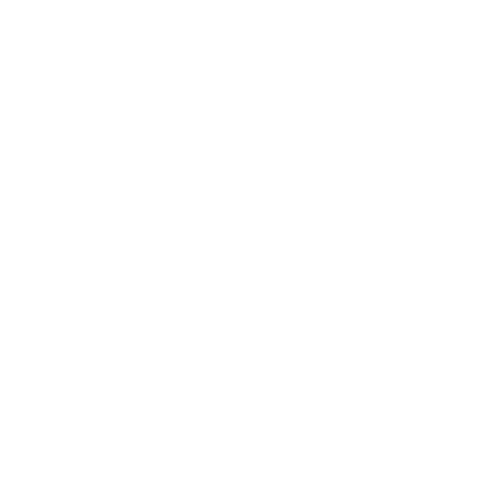学僧感悟|从求知的角度略探格物致知之义
2024-03-2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笔者读《大学》时,一直对格致之义不甚了解,查阅典籍,“格物致知”古来解释不一,大抵是以下四类为代表:
1、东汉郑玄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郑玄解读的角度不同于后世的理学和心学,是顺着下文“诚意正心修身”的脉络,解释为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意指事物善恶之来,在于人心感召,于善深则来善物,于恶深则引恶,并且在此基础上,人知善恶所至,故能抉择行善。
至于“格”字解释为“来”意,是因为“格”字源于“各”,甲骨文的“各”,上为倒“止”,下为“口”,原意为走近某物。“各”字加上“亻”,“佫”即为来、至之意。古书亦有借“格”为“佫”,表来到,到达。例如《尚书·舜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和《尚书·汤誓》之“格尔众庶,悉听朕言。”综上所述,郑玄解释,“格”与“致”二者义同,可为互训,格物为来物之意。但郑玄的解释,就不免产生前后文颠倒的问题,以郑玄所说之意,应该是先“致知”而后“格物”。
2、北宋司马光以物为物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故云:「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以格物为格除物欲。
3、宋明之后,对格物致知的探讨和分歧最大在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朱熹《大学章句》:“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即以穷物之理为格物之义。也有人解释“格”字为分辨之意,“格物”即为分辨人事之善恶。这两种解释,都是将“格物”与“致知”相连,偏重“求知”之意。
4、明代王阳明格竹不成,将求知的对象从外物转向身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之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解释致知亦别于朱熹,以良知为知,“致知曰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文中“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便是指朱熹对致知的解释。阳明反观自心,悟无心外之理事,故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其余古今诸家主张,无论从考据训诂还是从道理心性解释,得到的结果大多不出上文范围,文繁不列。

笔者以为,单以文中脉络而言,大学之道次第宛然:“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文中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儒家的“道次第”。若以因果而言,格物为因,致知为果,致知为因,诚意为果,而后正心修身,扩充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文中本末次既然第如此,那么读到这里,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问,是否未能格物致知的人便做不到诚意正心修身?若非如此,那格物致知的意义又在何处?
单从儒家的功夫论来说,古来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鲜少以求知做为修养身心的第一下手处,而更多从诚意正心、慎独修身开始修养自己,以达到明德至善。且《大学》文中也围绕着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主题而展开,不再解释格物致知。笔者以为无论是司马光所说的格除物欲还是王阳明的为善去恶显明良知,这些都已经是到诚意正心修身的日常功夫。
宋明的儒学,在心性方面的研究,受佛教的影响颇深。站在宋儒所探讨的角度看,就如同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比起切实可行的慎独修身,格物致知是上升到性与天道的层面。孔子亦言知命知天,只是弟子难臻其境,儒家君子多谈教育修养成仁取义,荀孟虽言性之善恶,其目的亦重在人文化成之道。直到佛教传入中国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始着力探讨天理、心性等哲学问题。
大学之道,现实功夫以慎独修身为始,而非从格物致知下手,如同佛教断十二缘起惑业苦之轮回,并不是从“无明”断,而从今生的“爱”断,当下对境的“触、受、爱、取、有”才是佛弟子用功之处。同类相比,“格物致知”对于“慎独修身”而言,是从生活当下更深一层探讨到生命根本、万法真相的问题。《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笔者以为,探讨格物的意义,重点在于如何达到致知。
致知之“知”,李翱解释为昭然明辨,朱熹理解为外在道理知识,王阳明解释为人心良知。理学心学家对所致之知截然不同的解释,便形成两种格物的思路和功夫,那究竟何者更合大学之道,何者更能切实入手?笔者以为,将《大学》上下文联系时,从佛法的角度看,可以将致知之“知”,理解为如实了知的智慧(般若)。从佛法的角度,也将智慧分为“涅槃智”和“法住智”两种,前者是空性无分别,后者善分别世间诸法。由格物,而有智慧,由智慧而臻圣人之境。
借朱熹解释“格物”的思路来说,《杂阿含》经世尊告诸比丘:“当正观察眼无常。如是观者,是名正见。正观故生厌,生厌故离喜、离贪,离喜、贪故,我说心正解脱。如是耳、鼻、舌、身、意,离喜、离贪,离喜、贪故。比丘,我说心正解脱,心正解脱者,能自记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佛教以五蕴、十二入,为行者观察的对象,此即是所格之“物”,佛陀教导弟子,应当正观察自己眼耳鼻舌身意无常,因为正观自身色法的无常,于是生厌离欲,心正解脱。不仅对于自己六根如此,佛陀教导四念处,亦是如此:
“比丘内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外身身观,精勤不懈,忆念不忘,舍世贪忧;内外身观,精勤不懈,舍世贪忧。受、意、法观,亦复如是。”
上面两段经文,可见佛陀教导弟子对身受心法、内外世界,如实了知,了知一切色法心法的真相,正念观见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以此于所缘境明忆不忘,念念相续,舍世贪忧,令心解脱。对比《阿含经》文再回顾朱熹解释“格物”为穷究事物之理,若将“事物之理”理解为一切诸法的共性,无常苦空的实相,便足以说得通为何穷究事物之理可以致知。王阳明格竹子不成,病在其只观竹子作为竹子假名安立的遍计所执,认假为真,而不能格到竹子乃至一切色法因缘所生无常败坏散灭的共性。王阳明所理解的理是事物特性就如现今自然科学知识,但物理化学知识又岂是坐在椅子上看七天能够格得出来?纵然真的被他观察总结出来竹子作为竹子的特性与规律,那他也只能是植物学家,而不能成穷究一切事物的规律法则的哲学家。然而阳明却因此悟到竹子无理可格,天理应从自身身心上寻求,明明德之功在诚意正心,格心之不正以致良知,如此达大学之明德至善,在某种程度上和朱熹也算是殊途同归。只是阳明未能破我法二执,所说的无心外事理亦非能所双亡,既然始终执着自己的身心意识又岂能明达诸法实相?
朱熹的解释观察外在事物,被唯物主义所采用。王阳明悟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而偏向了唯心主义哲学。《阿含经》中所教导的“格物致知”则比理学、心学家所谈要切实且深入许多。格物——穷究一切身心世界之理,可涵摄在四念处之中。行者不必先争论诸法是唯心还是唯物,若能在当下,观察到自身色法乃至一切色法如实的样子,见其迁流变化,生灭无住,正念觉知到诸法无常、苦、空、无我的共性,便足以照见五蕴世间的真相,放下贪染忧悲苦恼。格物之理与此同时便也完成了王阳明所谓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因为不仅色法如此,受想行识因缘生灭,刹那变化无常不住,一一皆是如此。看见自己心念念念相续的虚妄,悟其不实,便足以知善知恶为善去恶。那么理学心学家各自偏执的问题便也迎刃而解。
至于所“致”之“知”能达到的深广程度,笔者以为就“如实了知”的行法看,“致知”之意便可同“格物”结合一体,理解为如实了知,正观察了知一切事物实相。而从“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看,也可以将“致知”的境界拔高,理解为得法住智、涅槃智。行者若能做到当下正念正知正观察诸法,便是所谓格物,然后在正观察五蕴皆空无常无我的基础上,生厌离欲除世贪忧,智慧现行,便是所谓致知,了知一切诸法实相,得法住智及涅槃智。
法住智知诸法缘起流转,涅槃智知缘起还灭之理,二者涵盖世出世法。当行者通过正念观照诸法缘起性空,得证真实智慧,便是格物致知。行者有了格物致知的真实心地功夫,所谓“悟后起修”,那么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现实人生世间的实践,便可顺之而行,亦合于在明明德,在新民,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所以蕅益大师《大学直指》云:“致其知者,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格物者,作唯心识观,了知天下国家,根身器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心外别无他物也……知至者,二空妙观无间断也。”蕅祖以唯识观解释格物致知,其亦同于《阿含经》,皆以契入诸法实相得证真实智慧为行者所求之道。
儒家于“格物致知”聚讼千年,诸家各圆其说却各有所偏。但若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以“格物致知”为如实了知,转识成智,了知一切事物无常苦空无我的共性,达能所二空,破我法二执,得证实相般若。便足以阐明何以格物,致何等知。亦能将穷就事物之理,格除物欲,为善去恶致良知等解释一以贯之,涵摄在身受心法正念正观察的如实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