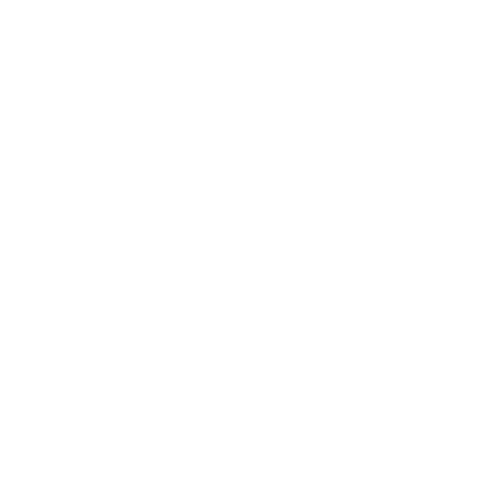学僧感悟|雪落封山 不必回信
2025-10-09
有一场雪,它只能下在离人的心里。这离,是出离的离。
赶在初雪前写信,寄往尘世一个未知的地址,收件人那一栏是空白。即使收到,也不必回信了,初雪后,我的心就已经封山了。而整座冬山也会全部融化在新的春天,所以不必按着过去的地址来寻我,更何况那时,我可能早已不在了。
年少的心事随着春华生长,随着夏日终结,随着秋风零落,随着冬雪埋藏,它的生住异灭从来都是悄悄的,我不敢有丝毫分心于它。它狂妄而不知分寸,得了几分光便要极放肆地疯长,不安分地蔓延,在拳头大小的心脏腔室内盘踞爪牙。我从来便知道的,若是稍稍着意了它,便要花大力气、大功夫去铲除它,它的根系牢牢扎进我的血肉里,拔除妄念的时候,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带出些热气腾腾的淋漓的血、带出些因见不得光透不得风而变得肮脏臭秽的脓汁、带出些它曾吮吸吞吃而赖以维持生长的腐肉。
本以为,出离正应如涸鲋得水、笼鸟脱樊,是悦意自适的,但只有亲历的人才知道剜肉医疮的疼痛吧?一些所谓的过来者言,又何曾提及那些切骨彻髓的痛呢?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那些未曾面对过湍急汹涌的奔流的人,又何曾感受过胼手胝足、入泥入水的苦,又怎么知道欲断流者的性命是那样悬若游丝,他们是独自站在四十里流前,以血肉之躯抗衡那裹挟着天地洪荒之怒的惊涛的。而这,仅仅是出离生死的第一步。

唔,但是你知道吗?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要告别少年的年纪里,我居然发现那个角落里的藤蔓、那吞吃腐肉脓血长大的、见了光便要疯长的妄想的怪物——它嫩嫩的触须上——开出了一朵花。是的,它开花了,开得和外面的花没有什么两样,是娇嫩的、无辜的宁馨儿,但我不敢去看它太久。它是光,是暖,是春天,但也是荆棘,是泥泞,是引人堕落的深渊。
我低头望着它,内心生出隐约的痛楚,就像某个遥远的梦,在浮尘未落的黄昏被轻轻拂起,像是少年时未曾开口的呓语,被岁月轻描淡写地覆盖,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微风掀开一角。
可是,我的心本该已经封山了。
大雪覆盖了入山的小径,封住了归路,也封住了那些未曾言说的心事。我以为只要足够冷静,足够克制,这一生便可以像一座山那样安稳,任风霜剥蚀,也不曾动摇。但空山之中,也会有不安分的枝丫,在漫长的黑夜里,悄然生长。
我曾以为出离意味着轻松,但真正的出离,反而处处是不能逃避的面对,更难、更需要勇气。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仰赖于戒律收束身口意,做到了正衣冠、持轨范、谨言慎行,但当夜深人静,四顾茫然,天地间只剩下自己时,那些缠绕骨血的东西,终究会慢慢浮上心头。
在我还是沙弥尼的时候,一位监学师父常常说:“严持净戒,无有毁犯,就能证阿罗汉果。”彼时年幼的我不懂,只是呆呆地点头,以为能持好戒,就真的后顾无忧了。可后来才慢慢发现,也许是我的根性陋劣?戒律约束了我的身体,却无法直接摧折我的妄念。妄念生起的刹那,它不问律藏,不论清规,不讲修行人的身份,它只是如实地来,如实地去,而在它逗留的时间里,你是否随它而行,便是功夫的分野。
显然,我的功夫还不够。
所以才会看着这朵花的时候,生出些许迟疑。它不过是小小的一朵,盛开在心中的阴翳处,藏在不易察觉的角落。若是放任不管,或许它会慢慢枯萎,但也有可能,等它结下种子,再次在某个措手不及的日子里,以更旺盛的姿态,破土而出。
我深知,它不能留。若不拔除,它便会成为心中的隐患,成为菩提道上的荆棘。这条路,本就是一条要放下、要割舍、要孤身行走的路。而真正的孤身,并不是身边无伴,而是心中无碍,赤条条、光净净,了无挂牵。
我曾以为,修行是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是要以无畏的姿态站在生死之上。但后来才明白,修行是无数次地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一次次地,从痛苦里拔出自己,从妄念里拯救自己。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勇敢的,我只是走得太久,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么,不必回信了。
初雪已落,整座冬山已经封闭,而春天的路,也不会再通向过去的地方。